本文目录一览:
如何看待信息茧房?
✨最近一段时间,“信息茧房”一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实这个词最初是由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提出的,网友也纷纷对这一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今天就来谈谈我是怎么看待信息茧房的:
🔴什么是信息茧房🔴
✍️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认为信息茧房是指在信息传播中,个人被禁锢在自我建构的信息环境中,只注意自己选择的领域,久而久之,就像被困在“茧房”中一样。我认为信息茧房可以用另一个词代替——就是大数据。
举个例子吧,就像今天的短视频软件,当我们长时间停在或者浏览某类视频时,大数据就会记住我们的喜好,然后会推荐更多类似的视频,而当再次遇到这类视频时,我们还是会忍不住点进去,最好我们的主页出现的就都是这种视频,这也是短视频造成我们上瘾的原因。其实不仅仅是短视频,我们的生活,如购物、音乐、新闻几乎所有方面都被大数据包围着。
🔵信息茧房的危害性🔵
容易导致观点片面化:
在“信息茧房”内,接触到的都是一些同质的视频,同时也会接触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在一遍遍固化和强调中,这种思想和观念就扎根在心里,拒斥其他观点输入,慢慢在这种环境中就形成了“沉默的螺旋”,也就是小部分人的意见趋同。
加剧思想的极端化:
处在信息茧房中的人接触的东西都是单一趋同的,并且缺少与外界和不同思想的交流沟通,所以长期看着内容同质化的东西就会形成固化的观点和思想,在信息茧中的人,坚信自己相信的,所看到的都是正确的,从而容易产生盲目自信、心胸狭隘等思维,甚至产生偏见。如果有一群人长期接受负面的、极端的信息,那些思想尚未形成或者容易受到影响的人加以效仿,并且影响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最终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造成群体间的冷漠:
在“信息茧房”中,人们很容易沉浸在自我的思想中,脱离了社会的发展,个体间形成一个个抱团现象,互不相信理解另一方的观点,最终导致人心涣散,个人之间彼此漠不关心。
🟡如何应对信息茧房🟡
合理运用媒介:
不同的媒介所传播的信息或者对信息进行解读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合理组合获取信息的方式,多在不同媒介上看看对同类信息解读的观点和看法,事后进行自己的反思,增加自己获取信息的渠道。
求同存异,不偏激:
当你意识到自己所听到的声音越来越一致的时候,这时就需要引起警惕,多去外面听听不同的声音。当看到和自己意见不同的观点时,先别急着反对或者站队,需要有自己思辨的过程,有一句话是:读书越少的人相信的东西就越绝对。所以,多去想想别人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观点。
不自我设限,保持好奇心:
信息茧房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我们喜欢的东西太单一了,不喜欢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尝试其他的东西。不愿接受新事物的人,其实本质上是因为承担力太弱而选择回避。所以我们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多去尝试自己没有接触过的领域,不给自己设限。
🙌总结:虽说在信息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逃不过算法和大数据,但是我们不能任由自己被困在茧中,多去接受一些多元的信息,多倾听一些不同的声音,努力成为破茧而出的蝴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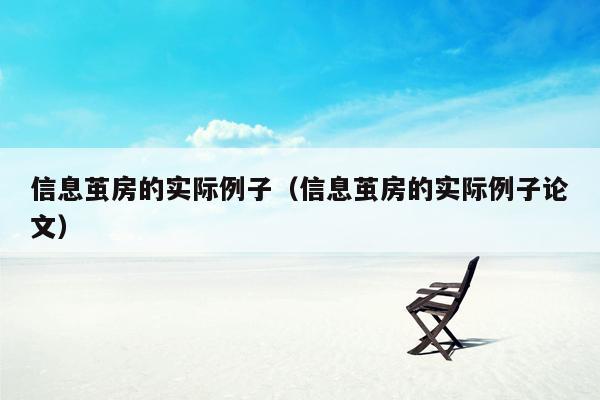
信息茧房通俗解释是什么?
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
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在社群内的交流更加高效的同时,社群之间的沟通并不见得一定会比信息匮乏的时代更加顺畅和有效。
预防
在防止网络茧房的对策方面,桑斯坦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监管上。通过政府积极的监管,让各类信息能够更均匀地传播,让受众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有用信息,有效的规避不良思想的传播,促使人们了解到社会的更多真实情况,对减轻极化和片面思想有很大的作用。
对于一些极端破坏性网站、极端思想人士的信息传播,政府要发挥监管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需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政府如何管制。将这一思想运用于高校公共网络平台,则意味着高校方面要积极承担起网络监管的责任。
高校必须要对校园网的网络平台进行规范,密切关注校园网络平台的舆论走向,有效屏蔽一些不良信息和极端偏激信息,通过积极有效的监管,实现校园网络的信息安全化、文明化。
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求高校在对校园舆论的敏感度上有新的标准,即对一般性的言论不要过度的干涉,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声音存在。如果高校在管理中把握不好尺度,对校园网络舆论妄加干涉,甚至自己制造舆论导向,这无疑是在制作一间更大的信息茧房,这将非常容易引起大学生的反感。
信息茧房的来源和意思 信息茧房讲解
1、来源于一个古老词汇作茧自缚的现代化说法,大数据在这几年特别的火,通常被各种大平台用来做数据分析,把你所想看到的广告、商品、内容等推荐到你面前,这样你的点击率就会大大增加了,而不是毫无目的的推荐一些你不感兴趣的东西。
2、信息茧房,是由于主观选择自己喜欢的消息接收,而让自己生活在自己选择的信息所构织的“蚕茧”内,用自己偏好的信息做蚕丝,作茧自缚。
3、信息茧房,这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但说直白点就是抖音的推荐算法。你会发现,你眼里的“别人的世界”,都是你向往的世界;别人,都是有趣的人;别人的老公,也根据你自己的选择偏好,呈现他们单一方面的特质,要么全是好老公,要么全是渣男。作为一个自认坐拥全世界网线的人,你自己蒙蔽了自己的双眼。
每天一个变好的小诀窍——和“信息茧房”说再见
你是否被困于“信息茧房”?
最近在阅读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语【信息茧房】。
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因为对新概念的好奇,我选择继续阅读下去。
什么是信息茧房?
所谓信息茧房,是指在信息传播中,如果一个人只关注自己选择的领域,或者只关注使自己愉悦舒服的东西,久而久之,便会像蚕一样,将自己封闭在自我编织的茧房之中。
文章还提到:
现在大数据兴起,算法越来越高级,可以帮你轻易过滤掉不熟悉、不认同、不喜欢的内容。
你看到的,永远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
你学到的,永远都是你认同的那些观点。
你听到的,永远都是你想听的那些声音。
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些网友反驳某个博主的观点,下面还会有一群人附和。
比如昨天有一个热搜新闻,赌王四房的小女儿何超欣从清华毕业,哥哥何猷君送上祝福。
下面有一群网友就在那边发言,说去年才入学,今年就研究生毕业了?
也有网友质疑何超欣的学历是妈妈“捐款”得到的,包括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科学位也是因为家里有钱。
很多网友也在下面留言表示赞同,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息茧房的案例。
人们只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相信自己认为正确的,而不管事实如何。
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采访,何猷君说自己的妹妹经常得数学金奖,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承认别人优秀很难,承认那些有家世背景且优秀的人更难。
只要你家底丰厚,你的成功就一定是因为家里。
这种惯性思维束缚着很多人。
我大学室友,父母都是80年代的大学生,并且都是当地央企的中层管理人员。
同学四年,还是大四毕业聚餐的时候她说出来我们才知道。
她平时是一个自主能力和目标性都很强的一个人。
喜欢旅游,考取了潜水教练证,靠教人潜水挣钱来筹集自己的 旅游资金。
毕业想去游轮上做摄影师,熬夜修片准备面试作品。
去游轮工作的理由也很简单,既可以免费旅游,还能赚钱。
在我们眼里,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她却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她说:“我父母朋友的孩子,要么国内985,要么国外常青藤。”
你看,明明可以靠家里,却事事都要自己去争取。
有时候你眼中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走出自己的信息茧房,扩大自己的视野。
我们最大的乐趣应该是不断的挑战自己,更新自己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内涵。
无论是对工作还是生活都走出自己的天地,到外面世界的富有和辽阔。
关于信息茧房的文献综述
(一)关于信息茧房的理论研究
信息茧房 最早 由哈佛大学的桑坦斯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信息乌托邦》中提出,其认为信息茧房 是人们只听人们选择的东西和可以愉悦人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信息茧房是指人们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1]。
彭兰在《人人皆媒时代的困境与突围可能》中提及了“社交过滤网、圈子与信息茧房”,认为信息茧房与人的选择性心理有关,在传统媒体时代就存在,但是算法新闻、对信息过滤的社交网络以及具有圈层分化的社交平台在今天将其进行了放大[2]。
喻国明在《信息茧房“禁锢”了我们的双眼》中介绍了信息茧房的概念以及其可能产生群体极化和社会粘性丧失的负面效应,并认为应通过完善技术算法和个人媒介素养两方面改善方式;他的另外一篇文章 《个性化新闻推送对新闻业务链的重塑》,从新闻生产和受众两个层面分析了个性化新闻内容推送对新闻业的重塑,认为走出“茧房”效应应按照用户的社交数据和相关关系来“定义”潜在的需求[3-4]。
陈昌凤教授与她的学生一同撰写了两篇论文《权力迁移与人本精神:算法式新闻分发的技术伦理》、《信息个人化、信息偏向与技术型纠偏——新技术时代我们如何获取信息》,前者分析了算法式分发新闻的现状,认为新闻分发权由人移交到机器、新闻把关权后移、公民参与受到损害;后者说明了信息平衡对于社会和个人的重要性,介绍国外现阶段的技术性纠偏尝试:新闻应用程序“跨越分歧的阅读”、英国卫报“刺破你的泡泡”、华尔街日报“红推送、蓝推送”等[5-6]。
对于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蔡磊平在《凸显与遮蔽:个性化推荐算法下的信息茧房现象》认为个性化推荐系统提高了信息分发率、满足受众信息需求但也造成了信息茧房现象,令受众的全面发展和对现实社会认知判断产生影响[7]。同类的还有胡婉婷在《“信息茧房”对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破坏》中分析了信息茧房对公共领域建构的影响,认为其使得意见自由表达受阻、公众理性批判缺失、社会粘性削弱[8];苏颖在《传播的权力偏向》认为信息茧房与从众效应是产生群体极化的主要原因,在突发事件中,网民的负面观点和非理性情绪在“信息茧房”得到进一步强化[9];郭小平在《信息的协同过滤与网民的群体极化倾向》中通过对网络事件的讨论得出了信息超载后的过滤会带来群体极化的现象,并对民主和理性沟通带来威胁[10]。
对于信息茧房的解决策略,王刚在《“个人日报”模式下的“信息茧房”效应反思》中认为个性化信息服务强化了“信息茧房”效应,扩大了知识鸿沟,媒体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提供高质量新闻内容[11];刘华栋在《社交媒体“信息茧房”的隐忧与对策》中分析了信息茧房的成因,发现社交媒体、个人议程设置、协同过滤算法三者为茧房效应的形成提供条件,提出了构建多元化信息接收渠道、构建人行道模式、提升媒介素养的建议[12]。
(二)有关信息茧房与具体案例的结合研究
部分研究多从具体案例的特点出发,结合信息茧房的相关概念特征进行质性分析。如杨慧的《微博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描述了信息茧房在微博中的体现并针对微博提出了相应改进策略[13]。许志源、唐维庸在《2016美国大选所透射的“过滤气泡”现象与启示》中以2016年的美国大选为研究事件,发现入们的“准感官统计”在新媒体时代受到技术算法的干扰,呼吁媒介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负起社会责任[14]。
在能够搜集到的国内定量方面研究中,李佳音在《基于个性化推荐系统新闻客户端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中选取今日头条作为个性化推荐系统的代表,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调查今日头条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信息茧房效应的影响[15];彭晓晓在《信息时代下的认知茧房》中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选取的微博样本用户进行编码、界定、挖掘,并结合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分析,以此验证“茧房”效应的存在性问题[16]。两者对于本研究都有很好的启发性,但前者选取今日头条,后者通过一个范围很小的“微博上广告业界与学界的意见领袖”群体来推定信息茧房的存在,在样本范围以及差异性上有些不妥。
(三)总结
通过对文献进行整理,发现现有关于信息茧房研究都是基于桑坦斯教授的理论,侧重于对于信息茧房的理论再认识,并且都停留于行为模式的简单陈述。部分研究结合了具体案例,但是仍是泛泛而谈地去佐证桑坦斯教授的理论和观点,没有对信息茧房现象提出针对性的建议,缺乏对于观众行为和信息平台的深入讨论研究。
(四)参考文献
[if !supportLists][1] [endif]李清池.通向信息乌托邦的道路——读《信息乌托邦》[J].中国法律,2010(02):19-20+73.
[if !supportLists][2] [endif]彭兰.人人皆媒时代的困境与突围可能[J].新闻与写作,2017(11):64-68.
[if !supportLists][3] [endif]喻国明.“信息茧房”禁锢了我们的双眼[J].领导科学,2016(36):20.
[if !supportLists][4] [endif]喻国明,侯伟鹏,程雪梅.个性化新闻推送对新闻业务链的重塑[J].新闻记者,2017(03):9-13.
[if !supportLists][5] [endif]陈昌凤,霍婕.权力迁移与人本精神:算法式新闻分发的技术伦理[J].新闻与写作,2018(01):63-66.
[if !supportLists][6] [endif]陈昌凤,张心蔚.信息个人化、信息偏向与技术性纠偏——新技术时代我们如何获取信息[J].新闻与写作,2017(08):42-45.
[if !supportLists][7] [endif]蔡磊平.凸显与遮蔽:个性化推荐算法下的信息茧房现象[J].东南传播,2017(07):12-13.
[if !supportLists][8] [endif]胡婉婷.“信息茧房”对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破坏[J].青年记者,2016(15):26-27.
[if !supportLists][9] [endif]苏颖. 传播的权力偏向[D].中国政法大学,2011.
[if !supportLists][10] [endif]郭小平.信息的“协同过滤”与网民的“群体极化”倾向[J].东南传播,2006(12):43-44.
[if !supportLists][11] [endif]王刚.“个人日报”模式下的“信息茧房”效应反思[J].青年记者,2017(29):18-19.
[if !supportLists][12] [endif]刘华栋.社交媒体“信息茧房”的隐忧与对策[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04):54-57.
[if !supportLists][13] [endif]杨慧. 微博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4.
[if !supportLists][14] [endif]许志源,唐维庸.2016美国大选所透射的“过滤气泡”现象与启示[J].传媒,2017(16):54-56.
[if !supportLists][15] [endif]李佳音. 基于个性化推荐系统新闻客户端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7.
[if !supportLists][16] [endif]孙亮.信息时代下的“认知茧房”[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0(04):52.